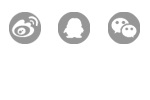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冷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是随着技术进步而产生和发展的,通过数字化方式,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和传播,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同时,基于非遗生命力维系的保护核心,如何正确看待数字化对非遗传承与传播的意义,我们还需要作理论的梳理。因此,在数字化热潮中,我们更需要做一些冷思考,才能把握好非遗数字化发展的方向。
数字化保存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文物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保存实践与相关研究都晚于图书文献档案领域,因而,在国内外非遗数字化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中,许多都来自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相关学科的高校、研究机构。纸质文献、静止图像、音视频等已有数字化指南与标准,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提供了实质性、前驱性的参考。但当我们思考数字化的目的,并需要明确数字化保存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时,显然不能直接照搬文献档案这类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价值,而是要回归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来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大分支,我们首先需要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出发,尝试确立非遗数字化保存的价值。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数字化保存隶属于“信息性保存”,被认为是冉冉升起的新门类。这类保护是基于“记录”的生产,这些记录可让观者进行虚拟体验。对于图书文献档案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信息保存即是保护的核心,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保护的核心是对遗产本体的保护。信息性保存能够在规避任何损害文化遗产的风险的同时,让观者体验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信息性保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其局限性。事实上,信息性保存并不会对对象的保护产生直接的作用,同样,数字化保存也无法直接维系非遗的生命力,尽管生成的数字资源可能会发挥出巨大的价值。
从非遗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的关系中,可以进一步明确数字化保存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非遗数字资源来源于非遗资源,但无法替代非遗资源。没有实体资源作为基础,数字资源将沦为空中楼阁。数字资源包含的信息不等同于实体资源所包含的信息,无法把非遗资源的许多无形的特征完全保存下来。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实现实体资源的最优化保存与呈现,同时,通过数字资源的有效传播来“放大”和“延伸”非遗数字化的价值。
传播是非遗数字资源实现保护价值的核心
2015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国际论坛”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在交流中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中国非遗相关数字资源的利用诉求。这种需求不止于目前可获取的基本信息的普及式传播,而是希望更进一步地公开非遗数字信息,以及实现学术研究层面的数据共享。在会上,多位国内学者则谈及了国内文化遗产数字化相关成果缺乏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机制,造成相同内容的重复数字化、重复数据分析问题。
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内不同的机构和组织都在不间断地做着基础性数据调查与数字化工作,其中包括信息的采集、文档的扫描、老照片的翻拍、音视频的转录等。但目前这些数据资源大多处于内部保管状态,由于知识产权等诸多顾虑,没能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可以说,非遗数字资源的传播,需要有更为开放、主动的现代传播姿态。就确保非遗生命力和自然传承的“终极目标”而言,我们在强调非遗数字资源保存价值的同时,更要挖掘其传播价值。
在开放的传播姿态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大众传播中的娱乐精神。例如,在非遗数字化传播中,利用视听语言、多感官语言、可交互语言等方式,为年轻人更轻松地描述与阐释非遗。例如,在传统节庆仪式类的非遗项目中,由于数字化对象是一个贯穿时空、多维立体的“文化空间”,所以,在音视频记录之外,在资金与技术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可尝试采取数字化多媒体领域的新技术手段,如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有时,我们要勇敢地用手中的媒介创造一些有关非遗的虚拟数字内容,当然,它们的内核是用来加深大众对非遗的理解。要知道,创造一些不借助技术就不能存在的内容,这一点在最初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中是并不被看好的。如今看来,就非遗的共享与传播而言,引进新技术实现超现实的、全息化的非遗数字资源访问体验,是非遗保护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也将逐步发展成为辅助保护与传承行为的重要手段。
正如2014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末尾部分所述:“与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基于网络的非遗数字资源,将越来越成为让非遗进入普通人关注视野的最佳途径,也将越来越成为非遗保存、保护与传承的主要信息源泉与实现途径。”在这并不算长的两年中,基于移动互联、社交媒体与网络应用,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速度超出预期。其中,较为突出的传播媒介包括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等。
基于主流社交媒体的公众账号,承担着信息传播的门户作用。例如,非遗相关的微信订阅号、公众号数量巨大,其中包括了数以百计的经过认证的公众账号,不少订阅号信息发布频率也很高。这些订阅号、公众号的功能定位包括:个人研究成果发布平台、公司法人资讯转载与业务介绍、地方工作讯息发布与公众参与、研究机构综合发布等。比如,浙江象山县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每日都有消息推送,逐个介绍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阐释质朴而到位;教育活动频度也很高,策划特别接地气。
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服务应用,承担着资源与服务延伸的功能。截至2015年11月19日,在APP Store上线的与非遗相关的软件已有十余个,比如在2015年成都国际非遗节时上线的“非遗宝”“非遗在中国”“非遗·四川”“长江非遗”“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Web网站、移动应用、公众账号等社交媒体和网络应用,对于普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好者的角度而言,可选择面自然是越大越好,但当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就需要理性看待它的传播效果与存在的必要性。比如,非遗电子地图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对应的是怎么样的使用需求?事实上,单一的非遗基本信息导览地图,多数情况下是缺乏吸引力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通过电子地图可以找到老字号店铺,就是检索“地点”的实际需求。但是,许多非遗项目没有所谓“门市”,可能只在某些特定时间或者周期性时间进行,只显示申报时留的“地点”信息并没有实际意义。
非遗数字化需避免流于形式
非遗的数字化由于起步较晚,行业标准、各地实践与应用研究都处于试点与探索阶段。但与此同时,在当前互联网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数字资源的存储、检索与传播方式都经历着翻天覆地地变化。非遗数字化保存与传播身处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方面,技术手段与传播渠道的高速更替使得存储、共享平台的投入风险不断增大,很有可能在还未做完数据验证和系统完善时,这一技术形态就已过时;另一方面,互联网“热词”不断冲击着刚刚起步的非遗数字化研究与实践领域。部分从业者一味追求与新技术的结合应用,使得一些非遗数字化应用项目流于形式,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功能设计和传播效果。以辅助传承、促进传播为目的的非遗数字化,实质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无论是口述史录音、抢救性摄录,还是日常性的资讯与资源网际分享,与技术、媒介的结合只是非遗数字化的实现手段,过于强调这层光鲜的“外衣”,非遗数字化实践就会止步于表面,对保护无益。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的“大数据”的作用,则被埃雷兹·艾登(美)和让·巴蒂斯特·米歇尔(法)所着的《可视化未来》一书点明了其短板,即:海量数据是由互联网催生的,因而都是新近记录,时间跨度很短。对于文化变迁研究而言,短期数据没有多大用处。也就是说当代现象研究可以利用“大数据”,人文历史研究却和一般性的“大数据”无缘。在历史和文学领域,关于特定时间和地区的图书文献才是最重要的信息源。
在非遗的研究与传播中,我们从“大数据”中只能获得当代的即时信息和当代人对此的认知信息。因而,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以及身体力行地去从事文献资料等的基础性数字化工作。这些资源形成的大数据,才能发挥革新人文历史研究方式的大数据功能。
孔子文化学院
- 18601王俊法——曲阜孔子文化学...
- 18401我院成立中华传统文化教师...
- 18096中华传统文化教师传承中心...
- 180642017年圣域同游国学夏令营...
- 18036COSE中华传统文化教师认证...
- 17927跟着孔子去游学项目简介...
- 17737古礼体验...
- 17690王哲——曲阜孔子文化学院...
- 17595数艺传承...
- 17375郭淑婷——曲阜孔子文化学...